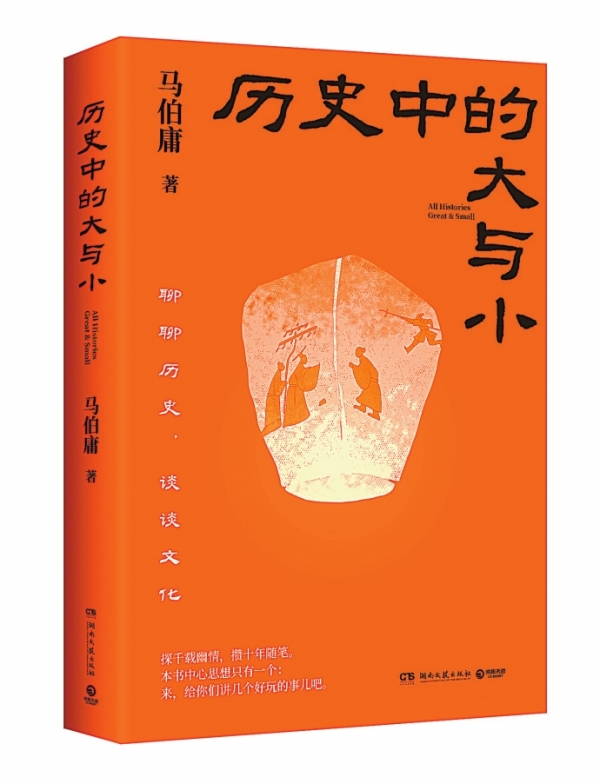
編者按
近日,馬伯庸全新歷史隨筆集《歷史中的大與小》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聯合出版上市。該書收錄馬伯庸跨越十余年的14篇歷史隨筆,這些文章如同散落的路標,標記了作者從靈光一閃,到考據梳理,再到文學轉化的全過程。
馬伯庸
如果說我有什么品質讓自己一直引以為傲的話,那應該是無用的好奇心。
2020年的春夏之交,我從南京坐火車前往滁州。車子剛一開動,我便習慣性地打開手機導航,觀察周圍的地名——這是我多年的一個習慣,在旅途中邂逅一些有趣的小地名,略做玩賞,聊以打發時間。當車子開過浦口不遠時,屏幕上赫然出現了一個名字,叫作“朱家山河”。
我霎時頭皮一麻,要知道,南京是大明故都,這里居然叫朱家山河,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,莫非當地有什么明代重大遺跡?我趕緊正襟危坐,恭恭敬敬搜了一下,然后發現誤會了……原來當地有一座山,叫朱家山,下面流經一條河。所以,正確斷句是“朱家山/河”,不是“朱家/山河”,我白激動了半天。
不過我又觀察了一下,發現這條河的走向有點不自然,便搜索了一下當地政府網站的地質信息。果然,這里本有兩條自然河,一條是連接滁河的北城圩古溝,一條是連接長江的黑水河。后經數百年的開鑿與疏通,兩河終于合二為一,形成一條滁河與長江之間的泄洪通道,如今是江蘇省不可移動文物。
本來到這里,玩賞活動就結束了。可我放下手機的一瞬間,忽然腦海里跳出一個疑惑:等等,幾百年的開鑿?豈不是說,這項工程橫跨了明、清兩代?整條朱家山河也才18公里長、河面20米寬,這點工程量用得著修那么久嗎?
我的好奇心又燃了起來,去翻找浦口當地的縣志,最終鎖定了確切的修建時間:這項水利工程從明成化十年(1474年)計劃修建,一直到清光緒十年(1884年)才竣工,前后四百一十年。好家伙,堪比大禹治水啊。那么,為什么會修這么久呢?我又翻檢出《來安縣志》和乾隆年間一位叫韓夢周的官員的記錄,才算把過程拼湊出來。
原來負責開鑿這條河的明、清兩代歷屆官員,要么貪贓枉法,要么尸位素餐,要么敷衍塞責,要么官商勾結,導致工程時修時停,十次無疾而終,從明中期拖拖拉拉到了晚清——所謂“或議而不行,或行而故謬”。直到吳長慶將軍重啟工程,左宗棠接手其后,又得張謇支持,三位當世人杰合力施為,才算把這條不起眼的小河徹底修完。這朱家山河,面子真是夠大的,其中的荒誕與曲折,小說都寫不出來。
完成這次小小的探索之后,我一抬頭,火車已到滁州。我揉了揉發酸的手腕,隨手把這樁小事發了一條微博,然后心滿意足地下車去參觀醉翁亭了。
我的朋友看到之后說:你打算寫本小說?我說目前沒計劃。我的責編看到,說這題材寫個非虛構也不錯。我說沒想過。一個記者在聽完這個故事后,動情地寫道:馬老師筆耕不輟,時時刻刻都在搜集素材。我請她把這句刪了,我沒那么熱愛工作,只是單純好奇罷了。
即使探尋的結果沒什么用處,但過程很有趣對不對?
這個小故事,只是我這些年走南闖北的一個小小插曲,類似的經歷還有太多。事實上,只要你對這個世界保持著好奇心,就會發現無論走到哪里,總有意外的驚喜。如果你除了好奇心,還具備了“勤快”這一品質,愿意把它們記錄下來,那么這些發現就會慢慢沉淀下來,最終變成一本書。
就是諸位手里捧著的這一本。
這是一本雜文集。注意啊,不是“雜文/集”,而是“雜/文集”,里面收錄的文章,都是過去十多年里我隨手寫的小文章,零碎不成體系,類型龐雜:有些是我陪孩子讀書時的心得體會;有些是我在旅途中偶遇的見聞經歷;有些是我在史料中挖掘到的有趣的故事,將之略做考據,重新敘述,算不得原創。
甚至連體例也未見統一。除了一些日常隨筆,本書還收錄了一部半的原創。一部是《敦煌英雄》,是一個電影的劇本。
半部是《盡意叮嚀滅寇仇——記一位壬辰戰爭中的抗倭英雄》,這篇文章是史實重敘,源自我在知乎的一個回答。后來我以這個回答為題材,寫了一個錦衣衛去日本的故事,被影視公司拿走直接拍成電視劇《日落東瀛》,但這個靈感來源,我覺得還是向大家分享一下。
這樣的文集,說是史論吧,失之于淺陋粗疏;說是游記吧,夾議的部分往往多于夾敘;說是嚴肅原創吧,旁逸斜出的腦洞又太多;說是戲謔小品,又嫌太長。如果勉強說它們之間有什么共同點的話,這些文章都沒什么用,都誕生于某種不帶功利、突如其來的好奇心,都是我在生活中一瞬間的興致所至。寫之前不知給誰看,寫完以后也不知登在哪兒。
這些無處安放的閑筆,是我對這個世界依舊充滿熱愛的最好證據。
責編:劉暢暢
一審:劉暢暢
二審:印奕帆
三審:譚登
來源:華聲在線








